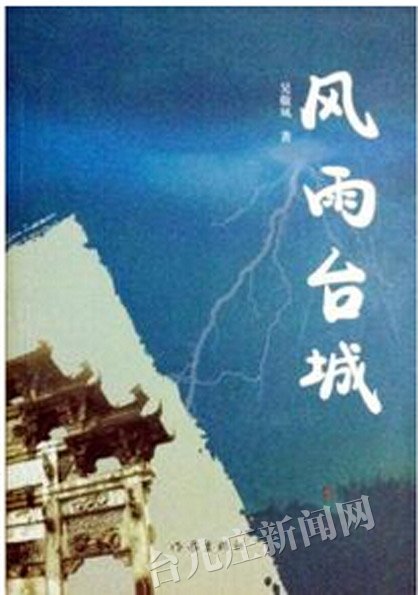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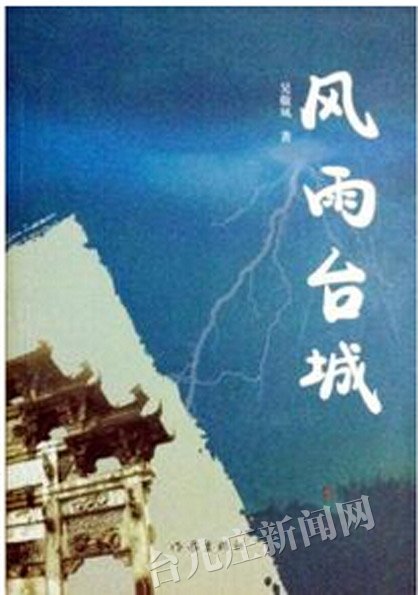
《风雨台城》,作者吴敬凤。古城由来久,已博天下名。长河横郭过,碧瓦覆琼城。群寺钟声远,孤帆落日红。清风才起处,幽巷酒旗升。这是发生在晚清及民国时期白黄两大家族的情长恩怨·名士方世云荡气回肠的一生给名震天下的台儿庄演义了一段精彩的故事。
《风雨台城》是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女作家吴敬凤继长篇小说《同命鸟》、《女人花》和诗集《似水情怀》后的第四部长篇巨著。该书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艺术地再现了运河古城台儿庄在民国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爆发的一桩桩跌宕起伏的故事,再现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通过逼真的细节描写,描画出当时的社会习俗和民间风情。该书已改编成40集电视连续剧《风雨台儿庄》。
《风雨台城》读后感
--台湾女作家郁馥馨
十几年前,父亲第一次回老家台儿庄探亲,回来带给我一本同乡文友的古诗词集,我也回赠自己的一本小说。就这样天南地北,我跟吴敬凤结识了。这么多年我们只见过三次面,但靠着书信往返和电话联系,一份难得的情谊显得深刻而绵长。
《风雨台城》是敬凤的第三本小说,我今年三月到苏州,收到敬凤的这本新书时,三月的苏州竟然还飘小雪。天气很冷,几乎不在我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当时双手捧着这本沉掂掂的书,不但有重量,也感觉很温暖。因为再度投入职场,又是完全不同的行业,我的身心都有点张罗不过来,这本书我看的很慢,都是白天上班前,边吃早餐边翻阅,还有晚上睡觉前当作精神食粮,慢慢咀嚼出书里人物在大时代命运里的巨大苦难,还有敬凤这么多年来在文学上的苦心经营。
有天晚上我看到白彦军(书中人物)这样磊落爽朗的人,为了替自己的兄弟赎罪,竟然毫不抵抗的被女人用剪刀刺死。我发了个短信给敬凤,说:“我很喜欢白彦军,他竟然就这样死了。”她回给我一条短信:“他的死代表一个美好时代的结束。”是的,以后日本人侵略中国,好不容易赶走外患,内战又起,堪称是中国老百姓最不幸的年代,多少英雄事迹、多少人间悲剧,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很难理解的。乱世出英雄,像方世云、段生林、李佩珍等,为民族大义不惜抛头颅、灑热血,但大部份的人再坏都坏不过赵不良,再好也少有人像褚思惠、宋老师一样忍受酷刑、宁死不屈。命只有一条,生活还是要继续,只恨错生了时代,有人忍气吞声,有人委曲求全,也想义薄云天,终究苟且偷生。就像赖二,就代表了大多数人。英雄非常人,最后在现实活过来的都是赖二这样的小人物。
另外,井小惠从一个善良、多愁善感的少女退场,再出现已经是个冷酷无情的日本军官,这是个很大的悬念,可以想见日本人在军事训练过程的残酷不仁,竟然可以把人性彻底催毁。可能资料收集不易,敬凤在这个转折过程没有交代,我觉得满可惜。
女性写作最大的困境在于缺乏眼界和想像力,很难走出自己窄小的天地;也因为特别感情用事,饱受感情的执着和束缚之苦。我是如此,敬凤也是如此。她之前的两本书《同命鸟》和《女人花》,尽管极力要创造出不一样的人物环境,但还是可以察觉出几乎一模一样的感情背景。写作最怕重复,这也是多年来我一直没写小说的原因。敬凤另辟蹊径,以家乡台儿庄为背景,以抗战历史为题材,不仅开拓了眼界,也突破了自己感情世界的窠臼。但既不能脱离历史,又必须有所创意,有时比写自己还难。除了勇气,还要有过人的耐性,我可以想见她花了近三年的时间成就这样一部小说,其中的过程,肯定相当煎熬。
历史有时见仁见智,真相常常各说各话,但是在历史长河的惊涛骇浪中载浮载沉的小老百姓的经历和感受,都是痛苦而深刻的。有人说小说即便有所虚构,但可能更贴近人性的真实部份。所以历史小说最难的是,它跟我们毕竟有段时空距离。敬凤这部小说的小人物,写这些人物在乱世的坚持或委屈,形象鲜明而深刻,也很能激起我同仇敌忾的民族情操。
我在看《风雨台城》这本书之前,正好看完《写作的女人生活危险》这本书。序言里有这样的一段话:为什么恰巧所有最聪颖、最具创造力、最有天分的女人都对自己的生活感到绝望,觉得无法再继续承受?显然地,保有爱情并同时进行艺术创作能让男人感到快乐,却足以摧毁女人。个中原因非常简单,却也实在让人难以忍受,男人之所以能够兼顾两者,是因为有女人照料他们的生活起居,让他们专心写作(或进行其它创作),那么,又有谁来照料女人的生活起居呢?男人非常乐于将女人看作创作的谬斯,那么,女人的谬斯又是谁呢?
敬凤的谬斯是谁呢?是谁让她在小时候受困於艰难穷苦的生活,不能接受完整的教育,却能自学有成,渴望创作的种子突破坚硬贫瘠的土地迎风逆长成文学大树?仍能坚守一字一句,把自己危险的生活发挥到极致?
是的,写作的女人生活危险。就像我也一次一次把自己陷入危险之中,我的精神很疲惫,我的心没有归途。但对我们这样不合时宜、不切实际的女人而言,不写作的生活同样没有出路。智利女作家伊莎貝拉阿言德这么说:你有很多事情得忙,別再自艾自憐了,去喝點水,然後開始寫作吧!
写给敬凤,就让我们在危险中相互扶持吧。
2010年6月20日
|
我认识的作家吴敬凤
-沈庆敏
吴敬凤,台儿庄区政协委员,民盟盟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枣庄市作家协会会员,台儿庄区作家协会副主席,枣庄市诗词协会理事,作品有诗词专集《似水情怀》,长篇小说《同命鸟》,《女人花》及长篇历史小说《风雨台城》等。
吴敬凤1970年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她小的时候,在村里不吃公分,按人头分粮食和布票,而她正好姊妹多,年龄小,人小吃粮少、穿布少,在村里竟然混了个中上等户。
那时吴敬凤的父亲过得很悠然,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记性却是出奇的好,每逢集必到集上专门去听书,晚上再一字不漏地讲给她们姊妹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其乐融融的情景,一直是她多年以来最温馨的记忆。吴敬凤的父亲不但讲书给她们姊妹听,村里的村民也爱听她父亲讲书,夏日的夜晚,繁星点点,村里的人凑到她父亲跟前,静静地听他讲古论今。有时兴致上来了,她的父亲会留下一两个最好好友,炒一盘醋白菜,在煤油灯下慢悠悠地品砸。
在吴敬凤兄妹五个当中,她的父亲尤其的偏爱她,每次从集上回来,总要按她的要求买些好吃的来。往下分发的时候,分给她的最多。买新衣服也是给她买的最多。以至于她对父亲产生的爱和依赖,有种离开父亲就活不下去的感觉。后来施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吴敬凤的弟弟妹妹们半大不大,光能吃不能干,还要上学。地里的活总是干在人家最后面,庄稼地荒了一块又一块,就是没办法把草除完。她的母亲整天犯头疼病,地里的活大多靠父亲,家境一落千丈!那时吴敬凤上三年级,为了给家里添一个劳动力,她的母亲就把她硬从学校里拽了回来。那时她十三岁,大人能干的烙煎饼、挑水、锄地、浇园等活,她样样拿得起放得下。
事实上,吴敬凤从七八岁就很会拾柴、拾粪,拾的柴禾够一家人一冬烧的,粪攒到春天时种菜园。辍学有一个多月,吴敬凤的班主任李修荣老师在去她家第三次时才见到了她,硬是劝通她的母亲把她领回了学校。侥幸又上了一年,不得不被母亲劝着又退了学,但仍然没多长时间又被李老师拽走了,好歹断断续续地上到五年级。吴敬凤的父亲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骨子里却有着文人气质和弱点。由于她的父亲身体羸弱,又不善于持家,包干到人后,家境与村里其他人家的差距拉的越来越大,三间茅草屋成天漏雨,又低又矮,七口人基本上硬是凑合着住。生活的窘迫以及人穷被人欺的境况,造成了她父亲心理上极大的落差,每天除了喝酒浇愁就是酒后骂人、乱摔东西。
那时,吴敬凤带着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兄妹四人挤在一张床上,她的弟弟老尿床,几乎夜夜尿,床上连个褥子没有,一泡尿下来整个床犹如被大雨淋过,湿漉漉的。特别是冬天,兄妹几个在床上睡觉根本就不敢伸腿,蜷缩着身子凑合一夜。那时吴敬凤就喜欢上文学,先是对书痴迷,买不起书,满村跑着到有书的人的家里去借。为了能在邻居家借一本《美人鱼的故事》的画册,愣是在人家等了小半夜,直到人家看完才美滋滋地拿回来,结果因为回家太晚,挨了父亲一顿臭骂。
吴敬凤十七岁时,在枣庄广播电台发表第一首长诗《乡村八月》,随后一发不可收,又在报社里发表自由诗和古体诗词。十八岁开始小说的创作,那种创作几乎到了入迷的地步,每夜2点之前没有睡过觉。导致后来神经衰弱,四肢无力,夜里做噩梦,走路发飘。每天喝得昏天黑地的父亲,看到吴敬凤虚弱的样子,认为她是有意偷懒不想干活,咬牙切齿地咒骂她。骂得全家人都恨他,恨他一天到晚搅得一家不得安生。
后来吴敬凤回想起来,才明白她父亲那时其实神经已经有问题了。她的父亲在他四十四岁那年以一根绳子在自家院子里的一棵枣树上了结了自己的生命。之前,他曾经自言自语念叨好长时间,哪种死法最容易。谁也没想到,他真的会死。他死以后,整个家庭的负担都压在吴敬凤的身上,她那时暗暗下定决心,弟弟妹妹不成家,绝不嫁人。世事多变,几年后吴敬凤成立自己的小家庭,但对于弟弟妹妹,一天未曾放弃责任,直到他们全部成家。后来吴敬凤有了儿子,家庭因生意的跌落,尤其是三角债拖累的已负债累累。一连好多年,家里从没有一天断过债主过。
写《女人花》时,吴敬凤租了一套很小的房子,常把门在里面反锁起来,通常上午写上一上午,下午出去借钱应付债主、经营生意。虽然现在吴敬凤的日子和生意逐渐走上了正轨,但仍有很多家庭及生意上的事务把她搞得像陀螺似地天天转,只得把写作的时间放在夜里。写《风雨台城》时,因长期熬夜,竟导致了神经衰弱和习惯性贫血。好多人也不无揶揄地问过她,到底为了什么?这个问题吴敬凤觉得不好回答。我认为自己写作确实没有写出什么。她说:“二十多年了,什么都没有写出来。但,人的一生,用最通俗的话来说,都有所爱。我只能说我爱。爱,不需要理由。人这一生,我觉得如果连梦想都没有,即使拥有的再多,都是不完整的人生。
”吴敬凤爱写作。她把写作当做她的一生情,一生梦,一生所求。生活的风风雨雨使她这只彩凤在一次次涅槃中获得新生的体验和收获,使她在写作的天空飞的越来越高远!
(责任编辑:bet365电脑网站) |